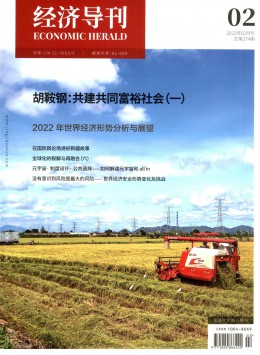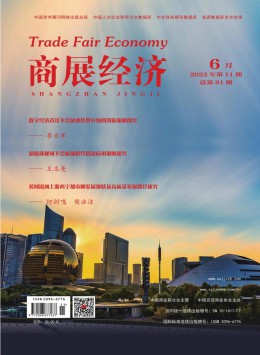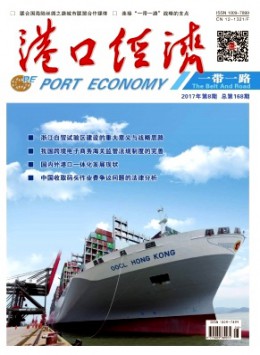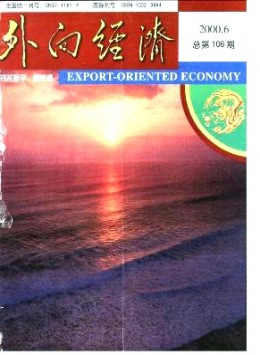經濟增長要素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濟增長要素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當今世界,各國都在大力發展經濟,并且依靠經濟的飛速發展來帶動整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然而,要實現經濟的快速持久增長,就必須在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諸如生產要素的投入、科學技術的進步、勞動資本的投入以及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等等。隨著全球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進一步發展,知識和科技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就知識和科技而言,又都屬于生產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實現經濟的快速持久發展,就必須加大在生產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產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在很大程度上反應和制約著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方式。就現在的經濟增長而言,單純依靠生產要素或其他要素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經濟的快速持久發展,必須依賴各種要素的共同作用。
對于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生產要素而言,必須要擺脫以前那種單純的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就能促進經濟快速持久增長的觀念。傳統而言,我們對生產要素的定義理解為:所謂生產要素指的是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時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資源,這些社會資源是維系一個經濟體國民經濟運行以及市場主體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各種基本要素。就學理意義而言,生產要素則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范疇。按照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界定,一般而言,生產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內容,即勞動力、土地、資本以及企業家。長期以來,國外學術界對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也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就我國而言,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績。在本文中,筆者將采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推薦的經濟增長核算方法,來對我國近十幾年來經濟增長過程中生產要素所起的作用進行估算研究,并且著重分析研究生產要素投入、科學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進而分析前面兩個方面與后者之間的關系。
一、估算方法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估算要素對其的貢獻,就必須有一個可以比對的經濟增長核算方法。就經濟增長核算方法而言,最為知名的莫過于被譽為“經濟增長原因之父”的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森的經濟增長核算方法。丹尼爾森將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七個方面,分別是就業人數及其性別年齡結構、勞動時間、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資本存量、資源配置狀態、規模經濟以及知識進展。在這七種因素中,他進一步認為知識進步是影響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原因,而勞動力教育水平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最為基本的要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每年也會根據經濟增長核算方法來公布其成員國的各種生產率數據。因此,采用經濟增長核算方法這一國際通用的方法來對我國的要素生產率進行核算與比較就會更具科學性,并且也在與其他國家相互比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筆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形式的方法。
具體方法是:
假設經濟增長的總量生產函數為H,那么就可以將經濟增長的增加值表示為各類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和時間的函數。運用公式表示,即為Q=H(k1,k2,L kn;l1,l2,L lm;T)(1),在這一公式中,Q表示經濟增長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別表示不同種類的資本投入,而l1,l2和L lm則分別表示不同種類的勞動投入,T用來表示時間。
假設經濟增長中各種類型的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可以加總為單一的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指數,并且用A來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則生產函數就可以用公式表示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數據說明
在以上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對于科學、準確、客觀的分析經濟增長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貢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在對各種生產要素的衡量過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簡單的一件事,而是極為復雜和繁瑣的,并且對這種衡量在不同的學者看來還有許多不盡相同的意見。因此,從這層面上講,對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數據進行說明就顯得尤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經濟增長中的勞動投入最為理想的標準就是標準勞動時間,這也是大多數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測算方法。但是,我國在這方面與之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當然,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有關此類的研究也在不斷地深入和系統化。目前我國在資本投入此類數據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資本存量總額或資本存量凈額來衡量。
綜合考慮到國內在此類核算方面數據的限制,筆者主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所收錄的數據對我國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進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測算在經濟增長中勞動、資本以及科學技術進步對其的貢獻。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數據衡量中,筆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國統計年鑒》中收錄的各個年份的各類數據,以此來作為比對衡量的指標。這些數據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估算結果中的GDP指數、勞動投入指數、資本投入指數、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以及各種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中的勞動貢獻率、資本貢獻率、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
當然,在對各類數據的核算方法的選擇上,筆者還借鑒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資料,比如在對資本投入的相關核算上,就主要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生產率測算手冊》中推薦使用的方法。采用這種方法來估算和衡量我國資本投入方面的情況。在資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資本服務物量指數與資本服務數量變化之間的關系,在勞動力提供勞動服務的同時,進一步分析資本存量在資本服務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來核算和衡量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對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經濟增長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目前對投入要素中估計要素產出彈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計量經濟學中常用的回歸方法,一種則是收入份額法。兩種相比較,各有其優劣之處。回歸方法是對各類數據進行分析的一種常用方法,同時也是利用統計學原理描述隨機變量間相關關系的一種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運用回歸分析的方法,一般來講運用起來極為簡便直接,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著很大的缺點,即需要在進行數據核算分析中假設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為一個常數。然而,經濟的增長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變量,因此在設定要素產出彈性為一個常數的時候,就已經對準確核算這些數據產生了極大的局限。也正是從這個層面上講,回歸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從而影響到準確核算數據的得出。同樣,雖然收入份額法不用將要素的產出彈性假定為一個常數,但是這種方法卻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競爭市場以及經濟增長過程中不變的規模收益。這些同樣會影響到最終核算數據的準確度和科學性,所以我們要進行系統全面的統計核算。
通過對資本、技術等要素的估計與核算,我們會發現單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經無法支撐起我國經濟的快速持久增長,因此就必須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技術進步來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同時,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還必須處理好環境、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變以往的粗放式增長為集約式增長,在實現當前發展的同時為今后更為持久的發展積攢后勁和動力。
參考文獻:
[1]李京文,D.喬根森,鄭友敬,黑田昌裕等.生產率與中美日經濟增長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2]鄭玉歆.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及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規律—由東亞經濟增長方式的爭論談起[J].經濟研究,1999,(5).
第2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關鍵詞:林業要素林業經濟增長概況與對策
一、林業要素投入的基本概況
林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近年來過度開墾和放牧導致了北方一些地區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為了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林業部門加強了相關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對林業要素的投入。
1.勞動力數量的變化
在林業建設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資源。至林業產業發展的中期,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林業的可控能力變強,所需的人工也隨之產生了變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賴人力轉變為“半人工半自動化”的現代林業工作模式,這種工作模式極度適用于現代林業的發展需求。同時產業結構的變化,使其節省的勞動力自由流向社會中更缺乏勞動資源的其他產業,為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優化提供了勞動力方面的優化條件。對于林業經濟來說,勞動力數量的變化也代表著林業產業中科技水平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林業科技進步的一種體現。
2.產業管理方式的變化
經過不斷的發展,林業的經濟管理系統不斷完善并趨于現代化,同時林業的產業總值也隨之產生了變化。隨著國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斷增強,林業產業的總產值在持續增長,通過這種增長變化,傳統的林業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于現代化林業生產的基本需求。經過現代新型林業管理模式的革新,當代的林業工程建設更加趨于科學化管理,林業的發展也能夠按照科學的階段規劃逐漸推進,完成不同階段的不同任務需求。這樣的管理方式也帶動了林業經濟的發展,是現代化林業產業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體現。
3.林業面積增加的變化
隨著林業產業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國的林業產業面積也不斷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業的公益行為也為我國的造林面積增長貢獻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螞蟻森林等,市場上的經濟型企業對于我國林業發展的無私幫助,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植被面積,對我國的環境綠化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近年來的合理規劃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國的經濟性林業產業不斷的發展,充分發揮了森林植被對于自然環境和生態經濟的促進作用。西北地區的戈壁與沙漠,其植樹造林的作用更加明顯,近年來西北沙漠地帶發展的紅杉產業取得了一些成績,西北沙漠中紅杉能夠有效的實現防風固沙,同時能夠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礎性的強化作用,這也是林業為我國實現“綠色增土”的階段性勝利。
二、促進林業經濟發展的相關對策
1.加大基礎資金的投入力度
相關部門應加大對林業產業基礎資金的投入力度。林業產業的資金儲備是其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發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門保持對林業經濟扶持政策的同時,應對林業產業的融資渠道也合理的放寬,以吸引民間資金流入,這樣能為民間資本進入林業產業提供基礎性的助力。民間資本的流入能使社會更加重視林業產業的發展,為林業經濟帶來一定的收益。政府相關部門對于林業企業也要有實質上的幫扶,例如在稅收上有一定的優惠政策等,這也是提升林業整體經濟水平的重要舉措,更為林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宏觀調控的優化整合。
2.強化科研技術的創新力度
林業企事業單位應該加強對科研技術的創新力度,培養創新型林業人才,對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術予以淘汰。在林業經濟發展中,科技是企業進步的象征,也是企業在市場中提高自身競爭力的基本核心,為了能夠提高企業的科研技術創新力度,科研部門應對林業產業給予一定的幫助。林業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我國國土環境和生態保護,國家要對此產業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項目扶持,對在林業領域有突出貢獻的科研機構與人才國家應予以鼓勵及資助,政府與企業應積極的將林業科研成果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并實現其科研技術的生產價值。
第3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關鍵詞:要素積累;結構變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6-0017-04 收稿日期:2009-05-11
一、引言
建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GDP增長率由改革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9.8%(1978~2007),遠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3.3%。是什么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這種高增長是否有可持續性?對這些問題,結構主義和古典主義觀點給出了不同的解釋。結構主義觀點從產業結構轉移、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流動等方面追尋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古典主義(還包括新古典主義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下省略)觀點認為要素積累增長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
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要素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能夠促進生產率增長,從而帶動經濟增長,因而增長是結構轉變的一個結果。呂鐵(2002)采用1980年~1997年全國及各地區的制造業樣本數據經轉移一份額法計算得出的結論是,由于勞動投入并沒有明顯地向生產率高增長的行業轉移,中國制造業的結構變化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影響盡管存在但并不明顯。王德文、王美艷、陳蘭(2004)以遼寧省560家工業企業1991年~2001年的調查數據為樣本,來觀察中國工業結構調整對工業企業效率和勞動配置的影響,其結論表明,中國工業結構越來越符合我們的資源狀況和要素稟賦,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得到不斷發揮,即結構變動促進了生產率增長。李小平、盧現祥(2007)通過擴展的shin-share方法檢驗了中國制造業在1985年~2003年間的結構轉移與生產率增長變動的關系,結果表明,南于在制造業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中勞動和資本要素并沒有向高生產率的行業流動,因而在此期間,中國制造業結構變動并沒有導致顯著的“結構紅利假說”現象。李小平、陳勇(2007)實證檢驗了1998年-2004年間中國省際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和資本轉移對生產率增長的影響,發現勞動力流動對生產率增長的促進作用不顯著,資本轉移對生產率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考慮Verdoorn效應后,勞動力和資本轉移對中國工業TFP增長的總貢獻較小。干春暉、鄭若谷(2009)在估算三次產業資本存量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1978年~2007年期間產業結構的生產率增長效應,結果表明,勞動力和資本的結構變動在此期間日趨加快,而產業結構的變化則比較平緩,中國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自第二產業內部的要素流動產生的進步效應。
與結構主義觀點不同,關于經濟增長的古典主義理論假設經濟活動在競爭均衡的條件下發生,部門間要素的邊際收益相同,因此部門間生產要素的轉移不能夠增加總產出,資源的重新配置僅僅發生在經濟擴張時期。據此,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長期作用的結果,部門間的要素流動被認為相對不重要。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利用索洛殘差法、隱性變量法和潛在產出法估算出我國1979年~2004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結果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我國1979年~2004年間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較低,僅為9.46%,而要素投入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高達90.54%。湯向俊(2006)首先在生產函數中不考慮人力資本因素,計算表明中國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為0.83;引人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外部性后分析表明,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仍高達0.67。鄭京海、胡鞍鋼(2008)對中國1978年~2005年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觀察到了在此期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總體下降趨勢,資本的平均增長率超過GDP增長率3.13個百分點,資本投入貢獻了中國經濟增長的67%。
實際上,對經濟增長動因的古典主義、結構主義二分法顯得過于絕對。其中。古典主義理論所忽略的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促進作用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確實發生了;而結構主義觀點忽視要素積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也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歷史相悖,如對日本戰后高速增長成因的分析就認為資本(特別是壟斷資本)積累和適齡勞動力人口的快速增長是最重要的兩個原因之一(林直道,1995)。實際上,推動經濟增長的真實原因可能涵括了古典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全部主要要素,即要素積累和要素轉移推動的結構轉變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只不過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這兩類因素對產出增長的影響力有所不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具體案例而言,要素積累、結構變動在產出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本文將通過實證來分析。
二、要素積累、結構變動與中國經濟增長
1 數據選擇與處理
實證分析的樣本區間為1979年~2007年,共28個樣本,數據見表1。應變量為當年GDP(y),選擇物質資本存量(k)、就業人數(f)、勞動力流動(cf)、物質資本流動(ck)和對外貿易出口年增量(e)為解釋變量來分析各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物質資本存量的計算過程為,將基年定為1978年,選用徐現祥等(2007)的估算結果即6054億元,以當年資本形成總額為當年資本積累增量;以當年資本增量與上年資本存量之和為當年資本存量,不考慮折舊;以當年年底就業人數為勞動力變量;勞動力流動變量為當年由第一產業轉移出去的就業人數,即當年在非第一產業就業的農村人口,計算方法為農村經濟活動人口剔除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而農村經濟活動人口數為農村總人口乘以全國經濟活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于第二產業的迅猛發展是工業化階段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反映資本結構變動的變量選擇為第二產業當年新增資本積累,數據選自干春暉(2009)計算的中國第二產業資本存量;考慮到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出口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將當年出口變量也納入模型,所有變量值均剔除了價格因素。為按1978年可比價格計算,除特殊說明外,各相關基礎數據均來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考慮建立模型時數據穩定性的要求,對所有變量作了取對數處理,分別得到ly、ly、ll、lcl、lck、le。
2 參數估計
(1)增長回歸分析
為了考察要素積累和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我們采取了逐步回歸的策略,即將要素積累變量和結構變動
變量逐步納入回歸模型。以上述策略先后得到4個回歸方程,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在只包含要素積累變量的基礎上,每一次納入新的結構變量均較顯著地提高了模型的擬合優度,這表明要素結構變動因素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已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要素積累因素回歸方程中,物質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投入表現出對產出增長的很大影響作用,回歸方程1表明物質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投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分別拉動產出增長O,73和0,57個百分點;納入結構變量后,回歸方程3、4均表明物質資本對產出增長的彈性下降至0,47,勞動力投入的彈性更大幅下降至0,04~0,06。回歸方程3顯示勞動力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第一產業勞動力轉出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拉動產出增長0,28個百分點,這個影響力在所有影響產出增長的因素中僅次于物質資本積累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勞動力投入增長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回歸方程4顯示資本積累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的彈性為0,015。
回歸分析表明,在綜合考慮要素積累、結構變動和外部需求因素的情況下。要素積累貢獻了中國經濟增長的63%。特別是物質資本積累貢獻了產出增長的61%,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其次,外部需求拉動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位重要因素。當前來看,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的貢獻還較小,不過勞動力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的彈性略小于物質資本積累而稍大于對外貿易出口對產出增長的彈性,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物質資本結構變動對產出增長的彈性為負,成為制約產出增長的因素;計算期內,勞動力轉移對產出增長的貢獻份額為12%,資本結構變動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為-2%,因此綜合來看,要素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為10%。
(2)狀態空間模型分析
通過回歸分析雖然能夠在總體上了解各因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著何種影響,但由于回歸分析得來的參數是靜態的值,因而不能反映各因素發揮影響作用的動態過程。為了理解這一動態過程,需要得到動態的參數,因此需要建立狀態空間模型。
三、結論及建議
本文在逐步回歸法和狀態空間模型方法的基礎上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要素積累、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到以下幾個結論:第一,要素積累特別是物質資本積累是推動中國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素結構變動對產出增長的影響存在但不顯著;第二,勞動力投入對產出增長的彈性在過去30年中變化很大,由改革開放前期的顯著影響轉變至近期幾乎為零,這表明所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優勢可能即將不復存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必須作出改變;第三,勞動力結構變動對產出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顯著,但近期其影響力增長開始趨緩,這顯示了當前因勞動力結構變動產生的效率改進已經達到一個極限,勞動力結構變動有待進一步優化;第四,資本結構變動對產出增長的彈性為負,究其原因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長期中資本積累過度擴張且過于集中在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內部的某些部門,而沒有流向生產率更高的行業和部門。
對發達國家的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在這些經濟體工業化的過程中,資本積累因素對增長的貢獻約為30%~40%,資了改革開放以來要素積累、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的動態影響,其中svl、sv2、sv3、sv4分別為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變量對產}H的彈性。從圖1可以看出,資本積累對產flJ增長的拉動作用呈現出逐期增長之勢,但自從2000年以來增長的勢頭已趨緩,不過仍是影響產出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勞動力投入對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在改革開放初期較顯著,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有明顯的下降,長期來看影n向力呈下降趨勢,至近期已接近為零。資本結構變動在改革開放的頭10年中表現出促進產出增長的作用,但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資本結構變動的影響發生轉變,不僅促進產出增長的力度迅速下降,而且轉變至制約產出增長。相反,勞動力結構變動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對產出增長的拉動作用不顯著,但1992年之后表現出較快的增長,直至近年轉為相對平穩,因而長期來看呈現為上升勢態。本、勞動力轉移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為20%(Chenery et al,1968;Chenery,1970;Robinson,1971)。但本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檢驗表明,改革開放30年來,要素積累特別是資本積累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素的結構變動對產出增長的貢獻很小,因為資本對產出增長的貢獻高達60%以上,而要素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的貢獻合計僅為10%,特別是資本結構變動因素對產出增長的彈性甚至為負數。這確實表明當今發達經濟體工業化過程中曾經一再演示的社會經濟結構上的轉折在中國迄今遠未完成,中國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還是通過粗放型增長方式得以實現的,不具有可持續性。這也意味著未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將由要素積累方面轉向要素結構變動方面,結構變動因素將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方面(要索積累因素仍是重要的一方面)。不過,為了這一增長途徑的順利實現,推動資本、勞動力結構變動的優化為當務之急。
第4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投入產出
作者簡介:王沙沙,新疆財經大學統計與信息學院,碩士,研究方向:宏觀經濟;
周勇,新疆財經大學統計與信息學院副教授,博士。
中圖分類號:F061.5;F1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38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3-92-03
一、引言
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于1957年提出,是經濟增長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即廣義的技術進步,是指經濟增長中扣除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大物質要素投入增長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產出增長的因素之和,即經濟增長中去掉資金和勞動力增長之外的余值。[1]其影響因素較多,包括技術進步、制度安排、經濟結構、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
投入產出模型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其基本思想最早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投入產出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投入產出表;二是投入產出數學模型,兩者密不可分,形成一個完整的模型體系。由于投入產出表反映了一定時期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數量關系,而這種關系正是由這一時期技術進步狀況、經濟結構和組織管理水平等因素決定的。因此,把投入產出模型應用于測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中,是投入產出模型應用的一個新發展。
一般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文章多用“索羅余值”法、Malmquist方法等方法。而基于投入產出模型測量全要素生產率(即廣義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文獻并不多見。李斌(2003)基于投入產出的行模型 X=(I-A)-1Y, 認為總產出的變化來自于兩個方面:一部分由最終產出的變化解釋,另一部分由技術進步解釋, 并據此測算了全國1995-1997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絕對數[2];李景華(2007)應用投入產出行模型 X=AX+Y, 采用國家統計局的1987年和1995年以1990年當年價格作為基期的可比價基礎價格的30個部門投入產出表,測算了1987-1995年間各部門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3]。胡振華(1995)在研究和實際編制企業勞動投入產出表的基礎上,利用投入產出技術測度了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4]。而用投入產出模型來研究新疆全要素生產率的文章幾乎沒有。本文應用價值型投入產出行模型,從中間流量矩陣出發,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對新疆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模型的設計與解釋
價值型投入產出行模型的基本關系:
AX+Y=X(1)
其中,表示總產出列向量,表示最終使用列向量,是直接消耗系數矩陣。直接消耗系數矩陣中的元素aij表示j部門生產單位產品對第i部門產品的直接消耗量,將aij稱為第j部門對第i部門產品的直接消耗系數。它反映了在一定技術水平下第j部門與第i部門間的技術經濟聯系,因此又將直接消耗系數稱為技術系數、投入系數,用它可度量全要素生產率。
由(1)式可以推導得到:
(2)
其中,(I-A)-1稱為列昂惕夫逆系數矩陣,也稱為完全需要系數矩陣,通常記為B 。該矩陣中的元素bij表示j部門生產單位最終產品對i部門產品的完全需要量,這里既包括對中間產品的需求,又包括對最終產品本身的需求,即對總產品的完全需要。
用B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下面式子中1,0分別表示計算期和基期:
(3)
可見,總產出的增量X可以分解為兩部分:第一項為B1Y,可視為由最終產出的變化解釋的總產出的增加;第二項為BY0,可看作各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引起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的變化所解釋的總產出的增長。
將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的變化所解釋的總產出的變化視為全要素生產率(即廣義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因為在投入產出模型中,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生產技術聯系是通過矩陣A,即直接消耗系數來建立的,并且通過計算B來反映國民經濟各部門、再生產各環節之間的間接聯系。在價值型投入產出模型中,A除了受生產技術變化的影響外,還受到價格變化和部門構成變化的影響。因此,若能消除價格變化和部門構成變化的影響,則不同時期的A所反映的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從而BY0代表的便是各部門全要素生產率所解釋的總產出的變化,即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消除價格變化和部門構成變化對直接消耗系數A的影響之后,通過(3)式,我們知道BY0表示各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令, ,則Wi為第i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額(n表示第n個經濟部門)。
(4)
λi為第i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5)
λ為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預處理
本文采用新疆統計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門投入產出表》與《2007 年新疆42部門投入產出表》作為原始數據。由于使用投入產出模型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消除價格變化和部門構成變化對直接消耗系數的影響,因此,必須對原始數據進行相應的處理。針對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根據《新疆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收集到1997-2007年間上述部門的價格指數對《2007年42部門投入產出表》中的數據進行處理,得到以1997年為基期的2007年可比價投入產出表。針對部門構成的影響,我們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為基準,將1997年、2007年兩張表中的部門均調整為相對應的30個部門,并對調整所涉及的部門的數據進行了處理,達到盡量消除部門構成變化對直接消耗系數矩陣的影響的目的。
(二)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額與貢獻率
通過(3)、(4)式對處理后的數據計算,我們得到表1的結果。從表1可以看出,新疆全要素生產率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影響是不一樣的。1997-2007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對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采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通用和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和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其他工業、電力和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及郵電、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23個部門帶來正影響,其余的7個部門帶來負的影響。這個實證結果基本符合一般的經濟規律,全要素生產率(即廣義的技術進步)使一些部門的產出率提高了,也使另一些部門的產出率下降了,并且正影響的部門數多于負影響的部門數。
表1 各部門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測算
之所以會出現部分經濟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廣義的技術進步)的貢獻為負值,是由于(3)式是由投入產出行模型(1)式推導出來的,投入產出行模型側重于經濟部門 i(i=1,2,…,n)作為產出部門時其全要素生產率對總產出的影響。對于投入產出表的中間產品矩陣來說,每一個經濟部門都具有雙重身分(既是產出部門也是投入部門),而經濟部門 i(i=1,2,…,n)分別作為產出部門與投入部門時其全要素生產率對總產出的影響往往具有反向的作用(這種反作用是通過直接消耗系數A的反向變動來反映的)。因此,如何綜合考慮經濟部門的雙重身分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總產出的作用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根據(5)式,計算得到新疆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總貢獻率為57.93%。在《新疆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研究》這篇文章中測得全要素生產率對新疆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57.13%,本文的研究結果與之研究結果基本一致。說明1997-2007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對新疆的經濟增長貢獻較大,這也與新疆的實際情況基本上是吻合的。
四、結論
本文考慮部門之間的完全消耗關系、運用結構分解分析模型的分解方法、使用投入產出模型來測算新疆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為實證研究,利用新疆統計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門投入產出表》和《2007年新疆42部門投入產出表》,考慮價格因素和部門構成因素的影響,對1997-2007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測算,并進一步得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總貢獻為57.93%。綜合分析,實證結果基本符合新疆經濟的實際狀況。
參考文獻:
[1] 王沙沙.新疆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研究[J].企業導報,2012,(22).
[2] 李斌.基于投入產出表對技術進步的測算方法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02).
第5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關鍵詞:要素稟賦;基礎設施、發展戰略;經濟發展;空間計量
文章編號:2095-5960(2014)02-0019-10;中圖分類號:F224;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經濟增長離不開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將成為今后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推動力。決定產業結構的是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結構是指地區所擁有的各要素稟賦的豐裕程度。某一地區要素稟賦結構得到改善,會促使產業結構的升級,而如果一個地區或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得不到改善,則會阻礙產業結構升級,使其偏離發展階段的最優結構狀態,經濟增長趨于緩慢。新結構經濟學中把要素稟賦及要素稟賦結構認定為最重要的變量[1]。在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過程中,要素稟賦的界定范圍所包含的要素不斷增多,由起初的自然資源、勞動、資本,逐漸加入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新結構經濟學指出基礎設施也應屬于經濟的稟賦的一種,產業升級要伴隨其相應基礎設施的不斷改進,否則會產生x-低效率,而使得產業偏離其同時期最優的產業結構[2]。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改善需要通過各省份和地區要素稟賦結構的改善來實現。而一些地區選擇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或資源依賴型產業的發展戰略,對促進經濟增長的要素稟賦投入以及基礎設施的完善有所忽視,出現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升級緩慢、資源配置效率低和經濟效益不高等問題。
本文建立要素稟賦結構指標體系,通過1991、2001、2011年三個時間點的全國省際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研究我國經濟發展歷程,并與實際情況進行對比,以研究地區要素稟賦、基礎設施與發展戰略選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探討不同時間點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結果證明,隨著時間點的推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與阻礙因素是不同的,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稟賦結構趨向于復雜化和高級化。
二、文獻綜述
對于要素稟賦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早期集中在對外貿易、專業分工方面,后逐漸轉向國內產業與經濟增長方面。鞠建東、林毅夫、王勇[3](2004)通過實證分析,證明貿易結構的決定在于要素稟賦與技術比較優勢。徐康寧,王劍[4](2006)以要素稟賦及地理因素為視角,通過雙邊貿易引力模型,證明要素稟賦和地理因素共同決定了新型國際的貿易格局。劉修巖、何玉梅[5](2011)通過我國制造業行業數據,分析要素稟賦與產業空間集聚的關系。而覃成林[6](2011)、李超[7](2011)等研究了黃河流域要素稟賦對經濟空間分異的影響以及對產業空間布局的影響,指出要素稟賦不同導致地區經濟發展的分異。徐春華[8](2011)通過研究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貿易結構三者關系,證明要素稟賦結構升級決定產業、貿易結構的升級。張紀[9](2013)以要素稟賦理論為基礎,通過研究要素稟賦,分析產業內分工的動因。2012年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全面闡述了要素稟賦和稟賦結構的最新定義,以及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吳勇基于2006-2011省際面板數據分析了要素成本對地區招商引資的影響。[10]
關于發展戰略選擇問題,巴拉薩[11](Balassa,1981)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說明比較優勢與產業升級的關系,指出在經濟發展初期一個國家主要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更有利于貿易出口,但是隨著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增加、技術創新等使得比較優勢增加,會推動整個經濟體的產業不斷升級。在我國,以林毅夫(2003)、孫希芳[12]、李永軍[13](2003)等學者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戰略,認為經濟發展要符合比較優勢理論,并內生于決定比較優勢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改善來實現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高端產業轉變,同時在外部沖擊下,產業政策的取向必須按照比較優勢調整產業結構,以減少金融風險。林毅夫、陳斌開[14]、劉培林[15]研究了發展戰略的選擇對城市化、收入差距以及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等經濟因素影響。林毅夫在新結構經濟學(2012)中指出采取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的地區或國家比其他地區表現要好,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失敗的原因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合理。
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研究,Anselin[16](1988)認為空間單元之間存在相關性,必須在估計過程中考慮空間相關性和異質性,進而更有效地進行復雜經濟系統的計量分析。在我國,林光平[17](2005)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對1978-2002年我國28個省區的人均GDP的收斂情況進行了測度,發現地區之間的空間相關性對各地區的影響是越來越明顯的。吳玉鳴[18](2004)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差異進行分析,表明各地區之間存在經濟空間依賴型。潘文卿[19](2012)研究了1988-2009年我國各省人均GDP空間分布情況,發現省際人均GDP相關性越來越明顯,且地區經濟空間溢出效應隨著距離的增加而減小。
本文以比較優勢理論視角分析地區經濟增長問題,并認為短期可變要素稟賦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解釋變量。除了資本存量、勞動力稟賦、科技稟賦,還應考慮基礎設施和制度影響。其中制度稟賦的測度方面,相比較以往大多數使用的財政支出規模作為測度標準,以衡量地區是否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技術選擇指數(TCI)作為測度指標更準確。本文把要素稟賦、基礎設施與發展戰略同時作為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核心解釋變量。同時發展戰略選擇關系到地區要素配置效率以及科技創新性,而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產業升級,需要合理的發展戰略進行戰略定位與引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逐漸成為主要經濟調控手段,市場外部性問題增多,這需要地區不斷完善自身要素稟賦結構,以保證地區產業結構逐漸向高端化發展。
三、變量測度
(一)要素稟賦測度
在要素稟賦指標建立方面,結合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新制度理論,引入資本、勞動、人力資本、技術方面的稟賦類別,由于本文研究稟賦結構的動態演進過程,而自然稟賦在中短期處于相對靜態,因而沒有涉及。各稟賦指標測度方法如下:
1.物質資本稟賦。由于流動資本很難測度,本文通過永續盤存法[20],對1990-2011年間各省的固定資本存量進行計算,計算1991、2001、2011年三個時間點各省人均資本存量,作為物質資本稟賦的測度標準。
2.勞動力稟賦。從勞動力投入量和人均人力資本存量兩方面對勞動力稟賦進行測度。借鑒何楓和陳榮[20]的方法,通過計算年初從業人數和年末從業人數的平均值作為年勞動力投入量。人均人力資本存量的測度方面,通過年均受教育年限,引用國內廣泛認同的Psaeharopoulos (2004)對中國教育回報率的估計數據,設定小學教育階段回報率為0.18,中學教育階段為0.134,高等教育階段為0.151,以此計算人均人力資本存量。
3.技術稟賦。技術稟賦可以從科研投入、科研產出、科研規模三方面進行測度,但由于全國各省級相關統計數據不全,現用萬人科研和技術服務業職工數作為技術稟賦的測度標準,因為該指標可以間接反映地區科研投入、產出和規模。
(二)基礎設施測度
隨著新增長理論的發展,國內學者多以研究基礎設施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來研究其經濟的外溢效應。基礎設施越完備的地區其投資環境越優越,本文把基礎設施作為投資環境稟賦。基礎設施通過外溢效應,起到降低運輸成本、提高勞動力及技術傳播、聯通和擴張地區市場、促進地區經濟集聚等作用,以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在基礎設施的測度方面,本文借鑒劉生龍、胡鞍鋼[21](2010)的方法,通過交通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三個核心設施的量化計算對基礎設施進行測度。交通基礎設施的測度,加總鐵路、公路兩大基礎設施長度除以各省國土面積;能源基礎設施以人均能源消費總量為標準;信息基礎設施以各地區郵電業務總量為標準。
(三)發展戰略選擇測度
通過技術選擇指數[1](TCI)對地區發展戰略進行測度。一個地區的制度決定該地區產業發展是否違背比較優勢戰略,是否以市場為基礎制度。如果地區產業發展不能與同一時期本身所具備的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產業相符合,那么TCI將比其他情況更高。因為如果違背比較優勢,忽視要素稟賦結構,那么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相對于其他情況下由于壟斷價格導致的壟斷利潤,同時政府提供補貼貸款和優惠政策以降低扶持產業的運營成本,使得增加值上升,但產業吸納勞動力能力沒有顯著提高,導致TCI計算公式中分子變大,TCI值增加。該值越大,說明地區發展偏離現階段稟賦結構所決定的產業結構越大,違背比較優勢程度越高,資源配置效率越低下,影響產業發展。
從現階段來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至關重要,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成為主要阻礙地區經濟增長的因素。這種發展戰略容易使地區忽視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資源過渡投入被選擇產業,配置效率低下,同時技術創新受到阻礙,使其對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作用減弱。另外,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方式可能導致業結構向單一化方向發展,產業結構偏離,結果是經濟發展滯后。地區長期要素稟賦結構無法得到優化,非選擇性產業面臨更多的市場外部性問題。未來落后地區發展應以市場為主要基礎制度,注重自身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充分發揮制造業先發帶動優勢,加大生產業等制造業配套產業扶持力度,增強制造業與配套產業的依存度,同時通過深加工、制造業服務化等延長制造業產業鏈,提高制造業產品附加值。對于資源壟斷行業應該適當地進行管制,合理增加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科技創新等要素的投入,促使要素稟賦結構升級,以減少經濟運行的外部性問題。地區應施行人力資本驅動型經濟發展方式。隨著產業升級的加快,這需要相應的人力資本的提升,以降低結構性失業,使經濟吸納更多的就業人口,社會總財富增加;對于基礎設施,不應盲目投資,盲目投資導致資源浪費,經濟效益差等問題的發生,最后地方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債務風險性增大。應重點建設經濟效益快、對產業發展作用明顯的生產性基礎設施,保障產品與要素流轉與經濟運行流暢,減少地區企業的外部性問題,加大地方企業外部性補償;當前發展階段,提高整體要素生產效率,需要更深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參考文獻:
[1]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171.
[2]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研究[J].現代產業經濟,2013(3):234.
[3]鞠建東,林毅夫,王勇.要素稟賦、專業化分工、貿易的理論與實證――與楊小凱、張永生商榷[J].經濟學(季刊),2004(10):28.
[4]徐康寧,王劍.要素稟賦、地理因素與新國際分工[J].中國社會科學,2006(11):67.
[5]劉修巖,何玉梅. 集聚經濟、要素稟賦與產業的空間分布:來自制造業的證據[J].產業經濟研究2011(3):16.
[6]李敏納,蔡舒,張慧蓉,覃成林.要素稟賦與黃河流域經濟空間分異研究[J].經濟地理,2011(1):20.
[7]李超,覃成林.要素稟賦、資源環境約束與中國現代產業空間分布[J]南開經濟研究,2011(4):33.
[8]徐春華.以要素稟賦結構升級促進產業鏈延伸:走出“比較優勢陷阱”[J]經濟研究導刊,2011(35):183.
[9]張紀.基于要素稟賦理論的產品內分工動因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3(5):9.
[10]吳勇.要素成本與中西部地區招商引資研究――基于2006-2011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2013(6):92.
[11]Balassa.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65(33) : 99-123.
[12]林毅夫,孫希芳.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兼評《對中國外貿戰略與貿易政策的評論》[J]國際經濟評論,2013(12):16.
[13]林毅夫,李永軍.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J]管理世界,2003(7):30.
[14]陳斌開,林毅夫.發展戰略、城市化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J]中國社會科學,2013(4):91.
[15]林毅夫,劉培林.經濟發展戰略對勞動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基于中國經驗的實證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3(7):25.
[16] Anselin, L,1988a,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
[17]林光平,龍志和,吳梅.我國地區空間收斂的計量實證分析;1978-2002[J]”轉軌時期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4).
[18]吳玉鳴,徐建華.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集聚的空間統計分析[J].地理科學,2004(6):18.
[19]潘文卿.中國的區域關聯與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J].經濟研究,2012(1):130.
[20]何楓,陳榮,何林. 我國資本存量的估算及相關分析[J].經濟學家,2003(5):31.
[21]李海崢,等. 中國人力資本測度與指數構建[J].經濟研究,2010(8):53.
第6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方式 人力資源 素質要素 分析
1 人力資源與經濟增長關系有關理論
“世間萬物,人是最寶貴的,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這是對人力資源重要性的精僻論斷。人力資源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緊密關系在一些經濟理論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于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Q=ALμKр
其中Q為產量,L和K分別代表勞動和資本存量,A, u,p為三參數,其中0
2 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
2.1 一國經濟增長方式受人力資源數量的的影響 一國經濟增長需要有多種資源的投入,而任何一種物質資源的投入都要求有適當數量的人力資源與之匹配。同時人力資源在創造社會財富時也要消耗自然資源,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要處理好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協調關系。
2.2 一國經濟增長方式受人力資源質量的影響 人力資源質量的內涵就是人力資源的素質,包括人力資源的身體素質、道德素質和文化素質,人力資源素質可以通過后天的教育、培訓和其它手段加以提高的。一國人力資源素質高,勞動生產率就會高,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就會加快,從而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2.3 一國經濟增長方式受人力資源配置的影響 合理的人力資源配置可以提高物質資源的利用效率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一國經濟增長的規模受人力資源的數量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與運行質量受人力資源的質量影響,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的發展受人力資源配置的影響。因此,人力資源在數量、質量、配置等方面對經濟增長方式均產生影響。
3 遼寧省人力資源素質要素現狀分析
3.1 遼寧省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較低 表1列舉出2006年北京、上海、遼寧三個地區的從業人員素質狀況。遼寧從業人員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占到76.5%,高中教育人口占到13.77%,大學專科人口比例為6.05%,從業人員中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占3.31%,受過研究生教育的僅占0.28%。與遼寧情況相比,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比例北京的為39.82%,上海為44.1%;高中受教育比例北京為24.47%,上海為27.50%;大學專科教育比例北京為16.30%,上海為13.39%;大學本科教育比例北京為15.99%,上海為12.45%;研究生教育比例北京為3.41%,上海為1.92%。
雖然同期遼寧各層次人員比例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明顯與經濟發達地區的北京、上海相比有較大差距。說明遼寧省從業人口的整體素質要低于經濟發達地區,同時也說明經濟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力資源素偏低,也就是從業人員受教育的程度偏低。
3.2 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較低 教育經費投入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教育發展的重要條件。遼寧教育發展速度較快,但經費投入水平偏低,預算外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能力較弱,致使辦學經費短缺,進而勢必極大地影響遼寧教育水平即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版。
據統計年鑒顯示,2004年至2008年,遼寧省教育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分別為12.99%、11.81%、11.73、14.07%、12.45%,同期北京的教育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分別為13.51%、13.78%、13.51%、14.38%、14.67%,天津的分別為14.77%、15.2%15.2%、14.74%、14.75%。全國同期的投資比例分別為11.82%、11.71%、11.83%、14.31%、14.395%。從數據中可以看出遼寧的教育事業費支出與北京、天津存在較大差距,雖經過努力差距在縮短,尤其是2007年差距只剩下0.3、0.7個百分點,但在2008年這個差距又擴大了,擴大為2個百分點以上。遼寧作為教育大省,僅僅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
3.3 人力資本的貢獻率較低 遼寧人力資本在1980-
2003年時期的貢獻率是17.01%,固定資產的貢獻率是77.28%,人力資本的貢獻率遠遠小于固定資產的貢獻率。從1980-2003年期間遼寧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而不是人力資本的投資。
4 遼寧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之人力資源素質要素的對策
4.1 加大國民教育的投資力度,建立三結合的人才投資模式 政府在國民教育中是主要的投資主體,要加大教育投資占GDP的比例,在教育投資上要舍得下本錢。企業領導者要從教育、培訓的投資能從根本上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進而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角度認識人才投資的積極作用。員工個人要從提高自身素質,加快個人發展,完善職業生涯角度認識教育、培訓投資的重要性。在全社會建立政府、單位和個人三結合的人才投資新模式。
第一,政府要加大初等義務教育的投入,防止新文盲的產生。在農村和城市較偏遠的地方政府要加大義務教育的宣傳,讓所有的家長都認識到送適齡兒童上學的重要性。同時,對貧困地區的適齡兒童采取減免學費的政策措施,減少家庭的教育負擔。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發揮職業教育在掃除文盲、提高人口素質中的積極作用。
第二,提高重點學科建設質量,加強高層次創新人才的培養。目前遼寧省的25個高等學校制定的89個重點學科建設規劃(包括9個共建重點學科)進行了規劃審核,明確了學科發展的重點投入方向,促進了學科的快速、穩定發展。遴選出的緊缺人才培養培訓工程項目也已經舉行了授牌儀式。在第十次學位授權審核的申報組織工作中,全省共申報增列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22個、博士點67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116個,碩士點412個;申報新增博士學位授予單位2個、碩士學位授予單位1個,學士學位授予專業50個。
第三,加強本科專業建設。為了嚴把本科專業建設的質量關,組織專家對遼寧省80個試辦期滿的本科專業進行評估。為進一步推進學分制教學改革,組織專家對全省30所進行學分制教學管理的學校進行現場指導和研討。為了推進大學外語教學改革,組織了36名大學本科外語系主任到英國牛津大學進行培訓,學習國外先進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和先進的教學技術。為了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協作精神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還組織大學生進行科技競賽、機械設計競賽、廣告藝術大賽等活動。另外,還對全省22所獨立學院進行專項檢查,為制定獨立學院管理的有關政策提供了依據。
4.2 建立人才市場,實現市場導向的人才資源配置 建立人才市場,使人才的產權明晰,保證市場導向配置人力資源功能的發揮。建設人才市場體系,在完善遼寧省區域人才市場的基礎上,考慮建立國際、國內人才市場,全方位吸引人才,以適應新世紀的發展需要。政府在人才市場上要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實現人才與社會資源的有序化結合。
4.3 政府在人才資源開發利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在作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時一定要把人才規劃作為一個中心任務,要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為基礎對人才進行宏觀布局、層次結構、發展規模的系統預測和規劃。結合經濟發展目標,對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作出合理規劃。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全方位引入競爭機制,創造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幫助員工制定合理的職業生涯發展規劃,使員工早日作出成績。
參考文獻:
[1]王宇,焦建玲.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研究[J].管理科學,2005.18.
[2]周亞,,姜璐.人力資源素質與經濟增長――一個模型分析[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6.11.
[3]鐘水映,簡新華.人口資源與經濟環境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4]左玉輝,鄧艷,柏益堯.人口環境調控[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
第7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利用單元調查評估方法對農業面源污染進行核算,并將其作為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壞”產出指標納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評價模型,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方法分析1993-2010年環境約束下中國29個省份農業TFP增長,并對其收斂性進行了檢驗。研究表明:①環境約束下中國各地區農業TFP在考察期內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長,并且該增長主要是由農業技術進步推動,但是各地區的農業技術效率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惡化;②從地區差異來看,環境約束下中國各地區農業TFP在增長的同時呈現東、西、中部地區依次遞減;③當不考慮環境因素時,全國范圍以及中、西部地區的農業TFP平均增長率分別比考慮環境因素時提高0.88%、1.71%和2.35%,但是東部地區卻比考慮環境因素時降低1.01%;④環境約束下中國各地區農業TFP都存在σ收斂和絕對β收斂,但是σ收斂趨勢并不穩定,σ值呈現出顯著的波動特征。
關鍵詞 單元調查評估方法;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環境約束;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3-00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3.011
第8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生產要素 勞動力質量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6-0051-05
經歷了近30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也面臨著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諸多制約因素和約束條件。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最新預測,本世紀中葉之前的我國人口動態有三個轉折點:一是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2006年開始進入穩定期,從2010年起趨于下降;二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011年即趨于穩定,2022年以后則大幅度減少;三是總人口在2030年前后達到峰值,預測達14.39億,隨后絕對減少。[1] 這個預測和現實也表明,“人口紅利”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勞動力比較成本優勢已經開始出現轉折點,有利的“人口紅利”決定勞動力結構將會提前發生變化,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結束。因此,與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本、勞動與要素生產率的三大動因相關聯的“勞動力與經濟增長”等問題值得特別關注。
一、 資本、勞動、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分析
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土地(或自然資源)、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土地(或自然資源)是進行任何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力是進行生產的載體,是體現勞動者本身的資本;資本是用于投入生產或經營、用貨幣表示體現在物質方面上的財富。但是,在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中,經濟學家認為,除了常規的生產要素投入增加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外,往往還有一部分增長不能由這種要素來解釋。也就是說,除了增加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外,國民產值函數的“殘差”(residual)因素也在起作用。實際上,這是一系列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綜合表現,人們稱其為“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簡稱TFP)。
經濟發展實踐證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入實現經濟擴張,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實質性提高的國家,盡管在一定時期也可能實現高速增長,但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如,前蘇聯曾經一段時期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由于其經濟增長是依靠生產要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實現的,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微小并呈現日益降低的趨勢,導致經濟增長不能持續。在20世紀50-70年代,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3.9%。在這個增長率中,生產率提高的貢獻份額為負數。資本和勞動力對增長率的貢獻中,有大約13%被生產率水平低下而產生高投入低效率。改革開放后,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到8-9%左右,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大大提高。在這一期間,我國逐漸步入世界市場資源配置軌道,擴大對外開放和提高貿易依存度。如,從1978年貿易依存度為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6年的70.8%。在1979-1984年期間,全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只有41.04億美元,2006年則達到735.23億美元,增加了18倍。由于大量物質資本投入和貿易擴大,逐漸提高技術層次,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所造成的人口紅利,我國經濟保持了長達1/4世紀的高速增長。
《世界銀行報告》(1999)對1978-1998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分析認為,在此期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9.5%的增長率中,物質資本對此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份額為17%,勞動力轉移貢獻為16%,全要素生產率為30%。10年后,國內學者李善同等在《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增長前景分析》[2] 中的分析較為客觀,認為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25年,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的增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因。按照索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核算”分析方法,① 測算出我國1978年以來三大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結果如下。
過去25年中,我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推動力是資本投入與資本積聚。1978-2003年資本平均增長速度為9.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3.2%,導致GDP年均增長9.3%中近6個百分點。相對于資本來說,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逐漸減弱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勞動力的增速明顯放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始下降到10%以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成為繼資本之后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因素,雖然部分時期較低,但整體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基本接近30%,始終保持了較高的水平。過去20多年,導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快速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在不同生產率產業之間和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重新配置,促進了整體生產效率的改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經濟增長的潛力,促進了效率的提高;對外開放、吸引外資以及自身的技術創新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教育水平改善了勞動力要素的質量等等。
目前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在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程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邊際效率逐步遞減的趨勢,提升空間有限;面臨“人口紅利勞動力結構即將結束”以及資源與環境等約束條件下,勞動與全要素生產率中的勞動力質量提高具有發展潛力空間。由此,我國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中“從技術層面上加大自主創新、從勞動力層面上提高勞動力質量”成為現實的必要。
二、 GDP產值與勞動力結構的非均衡分析
據資料,2006年我國GDP增長10.7%,達到20.9407萬億元。從總量上看,這是我國GDP首次突破20萬億元;從經濟增速上看,10.7%創下了自1995年以來的新高。但是,三次產業產值與勞動者結構存在著“非均衡”,以及呈現經濟增長率高、勞動彈性低的反向變化是未來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
(一)三產產值與勞動力構成比重的“非均衡”
GDP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在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均衡的,三次產業的GDP比重與勞動力就業結構基本趨于一致。從GDP分布結構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第一產業比重均在3%-5%以內;第二產業比重一般為30%左右;第三產業比重多為65%以上。相應地,勞動力結構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與產值結構基本相似,GDP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呈現均衡的、先進的結構水平。目前,我國約有近一半的勞動力還在從事傳統而低產值的農業生產。一方面,盡管50%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值僅占GDP的15%左右,卻為中國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作出巨大貢獻;另一方面,50%的勞動力僅創造了15%左右的GDP,低水平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可忽視的現實。與此同時,第二產業產值略超過50%,但它所吸納的勞動力卻僅占22%左右,即“22%勞動力創造50%GDP產值”。這既不是我國工業總產值虛高,也不是工業生產效率和運行質量提高的結果,是資本要素推動經濟增長和GDP增加的原因所在。我國三產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的“非均衡”(見表2)。
有關專家稱這種現象為“產值工業化”。[3]“產值工業化”最現實的注釋為,工業經濟增長中數量擴張大于質量提升,主要為資本要素的增加而帶來的GDP增加;GDP產值結構與勞動力結構的先進性沒有凸現和勞動力質量需大大提高;在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沒有形成良性互動;在“產值工業化”的背后勞動效率、節約能耗、環境保護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大力改善的問題。產值工業化是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前的準備階段,直接關系到技術層次升級、勞動力質量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問題,勞動力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
(二)經濟增長率與勞動彈性的反向變化
在技術與資本不足的前提下,增加勞動力數量可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隨著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增加,勞動力質量將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率與勞動彈性呈反向變化趨勢,即經濟增長率高,勞動彈性低,對勞動力質量的需求逐漸擴大。經濟增長的勞動彈性系數是可以測量勞動力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衡量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增長關系最常用的指標。它是指勞動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比值,即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勞動增長的百分點。用公式表示為:E=L′/G′,其中E為勞動彈性,L′、G′分別為就業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人們可以用勞動彈性來衡量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果,間接反映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5)、《中國統計年鑒》(2005)數據計算:
據統計資料,我國勞動力占總人口比重從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4年的57.9%,“人口紅利”直接的反映是大大增加了勞動力數量。1953-1957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勞動彈性系數達到0.397的數值,技術與資本的投入有限,勞動力增長貢獻大。到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進一步增大到0.541的水平,其后逐漸減低;90年代后減低趨勢明顯,減低到0.108的水平。2001-2005年,經濟增長速度年均為9.58%,但勞動彈性系數仍在減低,達到0.078的水平。上述數據說明,我國在技術裝備陳舊落后和資本缺口大的情況下,勞動增長率增加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隨著改革開放后的技術裝備的進步、資本集約度的提高,提高勞動力質量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時期。
三、 經濟增長與勞動力質量的均衡關系
經濟增長方式所決定的,勞動力質量的需求是不同的。粗放型或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對勞動力質量以及技術應用存在差異。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存在反作用,存在著高勞動力質量與高經濟增長質量均衡與遞進關系,如出現GDP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GDP增長率與勞動彈性的相對“均衡”,三大產業產值與勞動者就業結構一致;經濟增長率高,勞動彈性和勞動力質量也相應提高,進而提高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
(一)資本投入與技術水平層次的變化
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產業結構和資本投入導致技術水平層次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工業結構內部呈現出明顯的技術升級特征。這些技術升級和技術層次的變遷,由物資資本投入完成和可以直觀看到發生的變化。從不同技術水平工業部門所占產出份額來看,高技術產業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超過20%,增幅達到14.9個百分點。而以資源為基礎的產業和低技術產業的份額則有大幅的下降,以資源為基礎的產業從28.7%下降到23.1%,下降5.6個百分點;低技術產業從17.7%下降到9.2%,下降了8.5個百分點;中技術產業的份額則變化不大,略微下降1個百分點。① 見表5。
表5說明,資本投入不同,技術層次的變化趨勢是高技術與低技術比重的變化,低技術資本投入持續降低,高技術資本投入持續提高,中技術資本投入基本維持不變。與此相關聯的,以物質資本投入的變化帶動技術層次的升級,帶動對人力資本以及勞動力質量的市場需求。
(二)資本投入與勞動力質量的提高
與上述同理,一般低技術產業工人的人力資本成本不高,投入不大;擁有中技術產業工人的人力資本需要繼續維持投入,因為它涉及面廣,這是提高勞動力質量的關鍵;同時需要不斷加大對高端技術藍領產業工人的人力資本投入,適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一般而言,物質資本投入與產出是直接的關系;人力資本投入與產出是間接關系。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進程看物質資本的投入要先于人力資本的投入;從效果看物質資本投入的“政績”要直觀于人力資本的投入;但從社會效益看人力資本提高是轉變經濟增長的關鍵。舒爾茨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者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他認為,人力資本就是人口質量投資,是一種能力資本、人力素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經濟增長的源泉。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超過物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資本在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發揮著相互替代和補充作用;其三,“經濟增長余數分析法”證明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人力資本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增長主要取決于人的素質而不是自然資源的豐瘠或資本存量的多少,人力資本的作用遠比物質資本重要得多。在經濟社會中,勞動力質量具體表現為勞動者的素質、態度和技能應用等。無論是社會或個人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既體現勞動者本身的資本,也體現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資本發揮著比物質資本更為重要的作用。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如系統接受教育、崗位與技術培訓、繼續教育和企業文化的認同等等,其目的就是要通過人力資本去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和提高經濟質量。
在對深圳人口總量與經濟增長均衡關系的問題上,實證分析的結果是深圳常住人口數量增速與經濟總量、工業總產值的增速相比呈逐漸下降趨勢,表現為對數曲線。1978-1989年深圳經濟總量每增加1萬元,就要增加1.41勞動力;1989-1994年為0.288勞動力;1995-2003年為0.175勞動力。1979-1993年深圳工業總產值每增加1萬元,就要增加1.07勞動力;1994-1999年為0.233勞動力;2000-2003年為0.140勞動力。從總體上看,深圳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是逐漸下降的,這是深圳經濟社會發展中有機資本與技術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發生變化的表現。否則,深圳GDP總量的增加與勞動力數量的同步增加,將是深圳各項資源條件難以承受的。[4] (P164-165) 上述說明,人口、勞動力數量與國民經濟產值呈現對數曲線,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反映,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所要求的,也是經濟增長的動因中變勞動力數量為勞動力質量的轉折點。
[參考文獻]
[1]蔡P. 21世紀中國經濟增長如何持續[Z]. 中國經濟報告,2006-11.
[2]李善同,侯永志等.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增長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
第9篇:經濟增長要素范文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二、粗放型與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